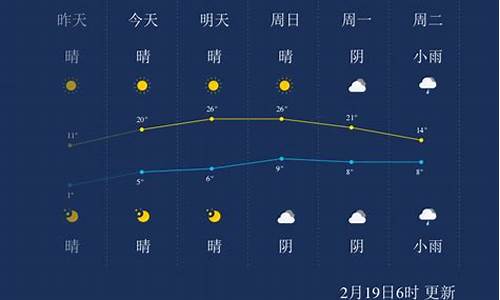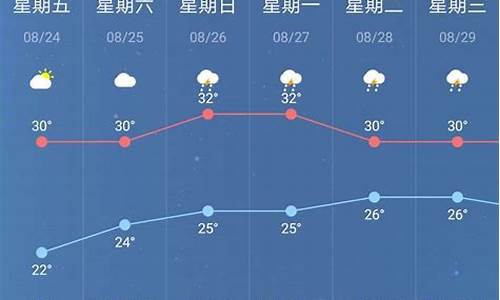上海天气余波_深圳天气预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后,提出“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引起社会各界对“灰犀牛”的关注和热议。相比大名鼎鼎的“黑天鹅”,“灰犀牛”这一相对陌生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有哪些典型的此类事件发生过?研究“灰犀牛”问题,对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带来怎样的启示?本报记者走访相关专家,试着为您作出最新解读。
“灰犀牛”与人们熟知的“黑天鹅”概念一样,“灰犀牛”是一个舶来品,它在国外被提出并应用也是近几年的事。
2013年1月,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在达沃斯论坛上,针对大概率、影响巨大的事件,首次提出“灰犀牛”概念,这个大胆而新颖的观点立刻触发社会学界尤其是人类决策与判断研究领域的极大兴趣。2015年,伦敦商学院知名教授迈克尔·雅可比基于渥克的提法,首次发表了系统阐释“黑天鹅”到“灰犀牛”趋势演变的论文,该文在国外刊载后被翻译引进,这也是“灰犀牛”首次出现在中国大众视野。
随后的2016年,渥克经过整理和研究,出版了一本颠覆人们既往认知的著作《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渥克提出,“灰犀牛”主要指明显的、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事件。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那些会对我们心理和情感造成冲击但发生概率极低的事情上,因此没能注意到那些发生概率极高、应该提早预防的事情。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的是“黑天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灰犀牛”。
“黑天鹅”可怕,“灰犀牛”也可怕被大多数人选择性忽视,错失最好时机,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也许很多人会好奇,为啥米歇尔·渥克偏偏选中“灰犀牛”这个概念呢?
“灰犀牛并非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是对概率大、冲击力强的风险的贴切比喻,代指没能及时阻止本来有能力、有机会阻止的灾难。”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介绍,灰犀牛体型巨大,本不该被忽视,但正因为其貌似愚笨粗拙,才让我们低估了它的风险,疏于防范。
生长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灰犀牛,身躯庞大,给人一种行动迟缓、安全无害的错觉,从而时常忽略了危险的存在——当灰犀牛被触怒发起攻击时,却会体现出惊人的爆发力,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最终引发破坏性极强的灾难。
“概率大、破坏力强是‘灰犀牛’事件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灰犀牛”事件的风险其实很容易被发现,却被大多数人选择性地忽视,或者将其当作一种正常的现象来认可或接受,以至于错失了最好的处理或控制风险的时机,最后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曾刚指出,从国外经验看,“灰犀牛”事件往往都是破坏力极强,一旦发生,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灰犀牛”风险的形成往往牵连甚广,要有效防范,从整体上进行统筹和推动,在制度惯性之下,这显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存在偏向性,容易低估风险,对即将到来的祸患视而不见,贻误了最好的危机处理时机。
“黑天鹅”很多,“灰犀牛”也很多很多危机事件,与其说是“黑天鹅”,不如说更像是“灰犀牛”
“灰犀牛”的提出,给原本为人们熟知的“黑天鹅”概念带来强烈冲击。在渥克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危机,并非发端于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黑天鹅”),而是大概率、高风险事件(“灰犀牛”)不断演化的结果,这些风险的存在早就广为人知,却由于体制或认识的局限,没有得到积极防范和应对,最终升级为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很多危机事件,与其说是‘黑天鹅’,其实不如说更像是‘灰犀牛’。”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认为,“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区分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互相转化。“黑天鹅”与“灰犀牛”犹如一对双生子,提醒人们对可能因为发生一些不寻常事件造成大震荡的大概率风险和小概率风险都应保持足够警惕。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平,在很多人看来,这场以雷曼兄弟突然倒闭为标志的风险事件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而现有的很多证据表明,源于美国“两房”(房地美、房利美)危机的风险,早已被频频预警,却被大多数人忽视。
2000年起美国房地产市场高度繁荣,房价持续上涨,住房抵押贷款规模不断攀升,在2007年达到总贷款的50%。2004年起美联储连续加息17次,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升到5.25%,房价终于在2006年底止升回落,刺破了房市泡沫,并触发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而早在2004年,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警醒人们提防抵押欺诈的大范围爆发;2007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不断发出警告;2008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风险报告指出,预期的房地产市场衰退、流动性资金紧缩和居高不下的油价都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推高了经济崩溃的风险性。这期间的先知先觉者并不在少数,圣路易联邦银行总裁威廉·普尔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议员理查德·贝克都曾预言房利美和房地美将出现大问题,但直到2008年“雷曼时刻”,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类似的还有卡特里娜飓风事件。2005年8月25日,卡特里娜飓风首次从美国佛罗里达登陆,29日再次登陆墨西哥湾沿岸新奥尔良外海岸,给新奥尔良市造成了极大破坏,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而当年1月,市政高官就已看到了一份详尽的灾难预防计划书,飓风到来前一个月还召开了关于飓风准备工作的研讨会,但政府推迟了飓风防御工作并拒绝采纳相关建议,最终飓风狂扫,造成巨灾。
渥克还认为,类似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这种突发事件,其实也是“灰犀牛”。从1977年起,航天飞机制造商就发现火箭推进器中存在一个设计缺陷,在外部环境温度较低时进行发射,可能导致严重的风险,就在发射航天飞机那个早晨,几位工程师还提出警告。但美国国家航天局没有理会这些警告,结果酿成悲剧。事后调查表明,只需要将发射调整到一个相对温暖的天气,所有损失都可以避免。
“风险总是被提起,却又总是被忽略。”董希淼指出,从国外这些“灰犀牛”事件来看,发生的关键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可预见的危机熟视无睹,不及时采取行动,终致重大危机。
我们身边有没有正在发生的“灰犀牛”?当然也有,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科学家们已经指出,二氧化碳浓度如果超过350ppm(百万分率)就非常危险,而2015年已经达到了400ppm。气候变化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尽管危害显而易见,但全球气候谈判举步维艰,近期美国更是一意孤行地退出了《巴黎协定》,让气候变化这一“灰犀牛”事件仍在不断向我们逼近。
“黑天鹅”要防,“灰犀牛”也要防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研究‘灰犀牛’,最终是要防范类似风险发生。”胡怡建说,“灰犀牛”事件是可防可控的,对这些风险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化未来的大震为今天的小震,一点点去处理,不要让其最后引发大的系统性风险,否则对经济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事实上,作为不同的风险事件类型,“灰犀牛”和“黑天鹅”有区别更有联系,不能将两种事件完全割裂,要从偶然发生的小概率“黑天鹅”事件背后,发现和防控必然发生的大概率“灰犀牛”系统性风险。防范当前金融风险,必须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
“党中央非常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始终要求守住底线,特别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王志军表示,“黑天鹅”和“灰犀牛”都有可能冲击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不同的思路和办法应对防范。
“黑天鹅”是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王志军认为,对这类事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运行基础尚不牢固的情况下,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跟踪监测分析和预警预测,及时发现一些经济运行中的趋势性、苗头性问题,未雨绸缪,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于‘灰犀牛’事件,因为问题已经存在了,也有征兆,所以对这类问题要增加危机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王志军说,对“灰犀牛”风险隐患,如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问题,应当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
“‘灰犀牛’是大概率、可感知的风险事件,应该成为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的重点。”曾刚认为,防范“灰犀牛”风险,首先要正视“灰犀牛”的存在,全面提高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风险意识。同时要统筹全局,制定防范和化解方案,特别是由于“灰犀牛”事件天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特征,政府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曾刚指出,“灰犀牛”事件的形成往往与制度缺陷或激励约束不当有关,在既有框架之下,难以阻止风险的进一步升级,必须诉诸体制改革和完善。“目前看,继续推进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防范此类风险的应有之义。”
海原县西安乡一位幸存者董善征说,“万家水的那山合了,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95岁的马成虎住在宁夏海原县城边上,他这一生居于此,只是宅院由土窑洞变成平房。百余米外,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万人坟遗址,经过90年的风雨侵蚀,仍隐约可见一处处连绵的坟包。未曾迁居他地的马成虎,仿佛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地震最后的守墓人。
“爷爷被打死了,叔叔被打死了。”面对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马成虎对五岁时经历浩劫的记忆仅止于此,他一家五口人,因地震而死去两人。这场以海原为震中心的大地震令海原县超过一半的人口失去生命。地震的波及范围非常之广,其中以宁夏南部的海原、固原,甘肃中北部的静宁、会宁、靖远、通渭、渭源,以及陕西西部受灾最为严重。
“这次地震有多大,我说几个现象你就知道了。”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对南都记者说,受海原大地震影响,波罗的海海面波浪浮动达几十厘米,而地震波的横波与纵波都穿过了地心,日本东京当时尚不太灵敏的仪器,还检测到地震表面波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原来说死了23万多人,也有说死了20多万,但现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死了27万多人。”
地震发生后的救济,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没有有效救灾。海原很多人都埋在万人坟了,好几个人埋在一个坟里。”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对南都记者说,当年海原的遇难者后代,也已迁徙到周边各省,每年的12月16日,万人坟这里会陆续从甘肃、青海、陕西及宁夏其他地方涌来上千名祭祀者。
但在海原之外,这场死亡人数超过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和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的浩劫,却并不为更多人所知。在汶川、玉树接二连三发生地震的当下,尘封许久的海原大地震被再度挖掘了出来,成为供国人凭吊与检视的标本。
在宁夏自治区政府的牵头下,建设中的海原地震博物馆将于明日———海原大地震90周年祭日举办开馆仪式。南都记者在现场看到,博物馆内部装修仍在紧张进行,尚未进行布展。刘刚介绍说,届时将会举办海原大地震学术研讨会,并请阿訇在万人坟上举办祈祷仪式。
“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
“1920年12月16日,大约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邻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名大约1200公里,而从海防到上海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名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许多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一些情况。在大名以北的板夏,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在距中国海125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走向市场的主妇们突然觉得晕船,北京和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样感觉……”这是海原地震发生后,苏联一位佚名作家撰写的《一九二零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
诚如郭增建研究员所言,整个世界几乎都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与南都读者更为相关的,在汕头外海,地震同样很强烈。有一艘从上海出发驶向香港的英国P和O公司的“D evanha”号客轮行至汕头外海时感觉到像地震一样强烈震动。“船长以为可能是船撞在了淹没的漂流物上,但等船靠了香港码头以后,他一检查船的外壳,很惊奇地发现,整个船壳都完好无损,这才想到了可能是地震引起的震动。”(据徐家汇观测台地震记录《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
和千里之外虚惊一场的插曲不同,处于地震中心的人们此时正经历生离死别的残酷考验。海原县九彩坪拱北幸存者冯志录,数年前对宁夏《在山走动的地方》记录片摄制组描述说,“老人们说那时间地摇时……我们那个地方把山嘴子一下摇着扑下来了,山洼里开的都是这么宽的口子。坐人的地方,山都塌着垒了下来。”海原县西安乡另一位幸存者董善征也说,“万家水的那山合了,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
在1922年第5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克劳斯、麦考米尔合撰的《在山走动的地方》报道,其中描述了海原大地震时发生的几个现象:在夜间移动的大山,似瀑布飞落般的山崩,陷进房屋和骆驼的大裂缝,以及把村庄席卷进升起的松软土海里的一切……
“海原大地震现在定为8.5级,过去也曾被定为8.6级。”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说,地震在当地形成200多公里的断裂带,有一个湖泊甚至因地面倾斜而迁移了几公里。黄土地质的山坡被震成粉末,形成黄土流,因为当地居民多住土窑洞,因此伤亡更显严重。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曾派郭增建等六同志组成地震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郭增建对南都记者回忆说,他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是,地震来时,天已变黑,因为没有电灯,甚至连油灯也比较少,很多人都待在家里。土窑洞口多被震塌堵死,有一个窑洞后来被老乡挖开,发现并没有被完全破坏,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因没有空气而憋死,死前似乎是在喝水,桌上一个碗里有油一样的东西,仿佛是人胃里的呕吐物。
死伤非常巨大。1921年4月3日《新闻报》报道称,“县城半边坍陷,甘肃海原县(海原彼时归甘肃辖下)旅京学生冯君翰英接到家函曰:”初七日黄昏地震,吾乡受害尤重,全城房屋俱被荡平,人民死伤十之八九,吾家花涯湾山庄,全行覆没,山崩土裂,山河更变……吾家四十余口,除父与汝祖母外,俱归浩劫。房屋倒尽,什物无存。全县死伤人民共计六万余人……‘“
“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的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4.5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8/10.半年后,翁文灏与谢家荣在“咨呈国务院内务部”的正式官方文件,则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7.3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
受灾第二严重区域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进行地震考察时,还能看见不少的地震遗迹:厚厚的砖筑城墙还在,南城门上刻着“镇秦门”几个大字(现城墙已经被拆除),该县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横截为二,上段与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转了方向。
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人。
12月16日的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倒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地吼如雷,声势极其危险。十八日风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后动者五次,均轻。十九日大动八次,地体日夜微摇不息。二十日大动十一次,小动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天气情况。其中,海原、固原等县下的一场大雪,冻死了无家可归的很多人。
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亦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孚,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动。郭增建说,1958年去考察时,听见有人说母亲在麦草堆里生下了他。
在公权力的触角尚未能抵达震区之时,灾民们依靠私力救济共渡难关。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县时,也听老乡们提起,大地震刚发生时,大家不分你我,谁家有现成的饮食都拿出来一起分享,过了几天之后,心理上就产生变化,各自考虑各自的未来,不再能随便去别人住处吃喝了。“在大灾面前,一开始有公心,后来私心居上。”郭增建说。
当姗姗来迟的政府救济终将抵达时,饱受冻饿的灾民常常也会不顾生命去索取。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乞,护押锅饼的士兵也叱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
“当时北京报纸,连震中地址都搞不清”
海原大地震来得突然,地方官署也受创严重,加上当时交通、通讯不便,一时之间难以组织救援。“兰州骑马到海原就要好几天,更何况道路都遭到破坏。县政府大概只有静宁等少数地方有记载救灾。其他的县府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政府也采取‘以工代赈’疏通道路,给灾民发放工钱,但都是少量的。”郭增建说。
当时的静宁县长是周廷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
周廷元并非自我夸饰,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廷元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然后回到室内跪下向神祷告,如神愿意的话,他愿以死来换取赦免群众……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
不过,大灾面前,由同样受重创的地方官府进行救助,显得力不从心。“那时救灾慢得很,在北京报纸上,连震中地址都搞不清,国外只说在那一段。通讯条件很差,又受到破坏,耽搁了好多天才知道。”郭增建介绍说,当时甘肃在京的商人、学生和国会议员等,向政府呼吁救灾,并在报上刊发了启事。当时募捐的人很多,在京亦成立紧急募捐大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献显示,甘肃省省长张广建曾以“十万火急”致函大总统,请求支援,但致函的时间已是地震过后一月余——1921年1月20日。在这之前,1920年12月29日,张广建也曾和甘肃省议会议长王世相等人向内务部致电求援。
“北洋政府可能也有贪污截留,地震发生前,正值华北五省大旱,有记载说死了50万人。当时有个说法,要救华北五省旱灾,政府赈灾的款给了国际组织。1921年初,甘肃留京人员在《中国民报》上揭露这个事,写得很好,痛骂北洋政府,大意是说,甘肃是为国家拿粮的省份,为何遇灾不救,好像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一样。”郭增建说。
直到1923年3月19日,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轮等人还在给中央赈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二年余的惨状:“敝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频岁歉收,始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近,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垣。”这些国会议员还提到,他们屡次接到同乡书信,获知甘肃灾民种种惨状,“竟有兰州有卖人肉包子之事”。兰州物价飞涨,而冬季接受施粥者已超过万人,虽然各界善款亦有施衣,但“饥冻以死者仍时有所闻”。
在这封函中,甘肃籍国会议员着重提出,赈务处应拨给甘肃的赈灾款“尚未及半”,希望体恤灾区黎民苦楚迅速补齐,“庶不至无告之民长此失所也”。由此可见,中央在赈灾问题上,截留应拨付的款项,问题颇为严重。
而甘肃省长,在海原大地震后两年多内,也换了多人,从张广建、潘龄皋一直到林锡光。“甘肃地方政府也有救灾,但据说张广建省长有贪污。”1958年赴海原等地考察的郭增建还听说,后来红军经过该地时,还曾批斗过涉嫌贪污赈灾款的人。
1920年12月16日,当时居住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一笔:“夜地震约一分时止”。
寥寥八个字,记下的是当时北京感受到的地震—仅仅属于可感级别,并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而这八个字,竟然成了那次大地震在北京最早的文字记录。
鲁迅先生不会想到,他记下的是千里之外大地震传导到北京的余波。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感受到了这次震撼。
在上海,天花板上的吊灯和吊扇长时间晃动,英国领事馆的时钟、信号钟都停止了摆动。
在香港,一位名叫福契特的神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清楚地感到床在晃、纱帐在动。
在大名以北的板夏(音译),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
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地震仪上也清晰地刻画出了异常的地震波。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有类似的记录。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海原地震的地质工作者。他说,当时对地震监测最严密、技术也最先进的是地震多发的日本。位于东京的地震仪检测到地震表面波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数小时后又转了回来,再次被记录下来。
东京地震台的仪器可以把地震波放大12倍,在当时是最灵敏的。
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强。
监测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台都有同一个问题—震中在哪里?
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地震台依据震波数据,推测说此次地震震中在距纽约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推测实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着地球表面计算,而是直取地球直径,偏远的海原距离纽约也远远超过3000英里。
对震中推测相对较为准确的,是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
徐家汇观象台是由法国教会组织建立的,当时由神父盖尔基(音)主持。徐家汇观象台就地震所作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详细记录了当天紧张的监测情景:
钟表突然停摆,而吊灯奇怪地摇晃起来。与普通人相比,他们(传教士)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急忙涌入安装有地震仪的地下室。
地震仪上的笔尖正在画着越来越宽的曲线,第一波较早的强波动出现在20时9分16秒。稍有平缓之后,地震仪上的南北向放大笔被剧烈的震动抛向了一边,盖尔基神父发出了警告:“注意!波动主峰就要到达了。”
这些波在20时16分到达。令人惊叹的是,震动的强烈竟然让地震仪都难以承受,笔尖半途跌落了。
虽然没能记录下全部的地震波,但已能够对地震的量级和位置进行推测。
震波在大地上涌动需要时间。宁夏地震局副总工程师柴炽章告诉记者,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它们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地震仪就是分别记录这几种波,然后根据它们到达的时间差、振幅等数据,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强度。不同位置的地震仪推测的地震震中范围不会完全一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推测,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离大概是1400公里。
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对震中的推测非常一致:甘肃东部(当时海原属于甘肃省,故又称甘肃大地震)。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